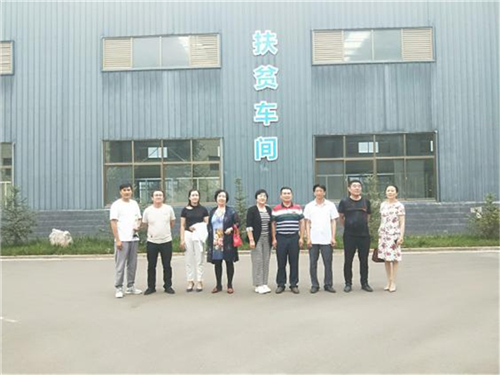图文/老炊
仲秋,从赛山归来,一脚踏进了熊湾。
倘若不是村前的那棵古树,我怎么能相信,眼前的这个村庄就是我记忆深处的那个熊湾呢?
豫南的村庄,有个特点,总是在村庄的名字前带着姓氏。然而,多数的村庄里,居住的又未必就是这个姓氏的居民。熊湾,从我记忆开始几乎全是李氏人家。这也足以说明了村庄历史之悠久和居住的变迁。
位于赛山北麓的熊湾自然村,隶属于美丽的凉亭乡保安村。这里山清水秀,遍地绿茶。这里是茶的故乡,著名的信阳毛尖茶“赛山玉莲”就产于此地,有着“西湖龙井”之美誉。油桃、板栗也一直是这个村庄的传统产业。
离开这个村庄四十几年了,四十几年里,村庄却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是我预想之内的,也是我预想不到的。
四十年来,中国乡村,一座座村庄在渐渐消失,一座座村庄又在修复中崛起。
熊湾是个较大的自然村,在各个方面一直有着一定的影响力。熊湾的变化,走在村庄修复的前头,尤其是对我来说最具意义,带来了我对村庄认识的新视野。它不同于那些典型示范性村庄的建设,熊湾完全定义在居住、生产、生活的需要上。
新砌池塘、河流、小桥,新建的别墅,灰砖新铺的村庄的地面连通着一个个弄巷……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设施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人文性的价值倾向在乡村开始萌生。

我和熊湾是有着深刻的渊源的,我认识熊湾、行走于熊湾主要是在我的少年时代。因为姓氏的原因,在这个村庄里,有一位我称作“大爷”和一位我称作“小爷”的两位长辈,故事主要是从他们谈起,说来话长。
虽然他们是我们家的远门自家,但大爷是我二叔的干爹,自然要亲如一家。于是每年拜年是必去的。幼小的我就这样跟着二叔走于熊湾。大爷是村支书,后来退位了,在村代销点里负责经营。大爷有四个儿子,已经都分开居住了,共四家,大爷和小儿子居住在一起。每年的拜年,四家都要去的,有时还要住上一宿。管饭,是过年中最重要的礼节,即便是临不上管饭,也要在中途“过个待”(方言:临时性吃点便餐,以表招待过)。那时大爷的家庭是很困难的,其实全村所有家庭都是很困难的,温饱都很难保证。大爷家的四个叔叔都先后分开居住,都需要房子的,房子是困扰家庭的第一难题。那时熊湾村的房子多是土坯房,也有茅草或稻草的。如果是雨天,村里的泥泞是该村最显著的特征,从这家到那家,通行主要是靠“高脚马”,绝大多数农家是买不起“皮筒子”的。在熊湾拜年,最怕的是天阴,雨后的半月,村里依然是泥巴。

后来,大爷去世了。我们就很少去熊湾了。再后来,我二叔也去世了。对于熊湾,渐渐成为我们童年时代留下的记忆。
对于熊湾的记忆,除了泥巴,还有村庄塘埂上的那棵古树,尤其是古树上还生长了另一棵柏树,我们感到无比的新奇,也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想象的思维。每年去熊湾,我们都要在古树下停留很久,似乎没有来到古树下就不算是到达熊湾。直至后来,乃至今日,那棵古树,依旧是记忆中的熊湾的化身。
四十年后,再次站在熊湾的村庄的这棵古树下,自然又想起了已去的大爷,他那不善言语的表情,就像这棵古树,任凭风吹雨打,总是沉默不语。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的时候,他却离开了人世。

村庄得到了修复,让我无法辨认。我有意走到村庄的前前后后、边边角角。找不到昔日的那个牛栏、那个猪圈、那个破碎的茅缸、还有那堆冒着袅袅烟雾的牛屎粪堆?但村后边保存着的那几座土坯房让我倍感亲切、倍感珍贵!走在村里,我认不出所有的人,自然所有的人也认不出我,只是微笑着,算是打了过招呼。我也无需去询问大爷家四个叔叔曾经的老宅地和现在的情况,看着村庄的现状,还有什么可问的呢?村庄得到了修复,但大爷早也离去,生命却不能复返。
古树得到了修复,与我依然是那么亲切。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古树,留下了岁月的千疮百孔,人们用混泥土填铸着她的累累伤痕,给予她新的养分,牢固着她向上的信心。她的枝叶伸向空中,苍翠遒劲,在仲秋的阳光下从容安静。遗憾的是,那上面曾经生长的那棵柏树却不见了,是人为的除去?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而死亡?接纳,包容,多元,互补,对历史的传承,对新生的保护等等,都应该是修复的元素、修复的意义。

秋日的阳光照耀着古树的枝叶,金色的余辉洒满我的周身,我倏然感到年轻了许多!
走在熊湾这棵千年古树和新生的别墅间,我突然想,我们李氏家族,不!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也应该得以修复,站在人类最文明的台阶上,与时俱进!
转载:紫弦之光 图文: 老炊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