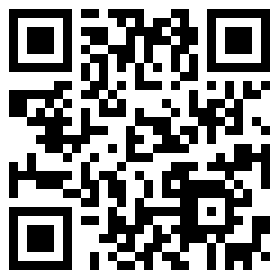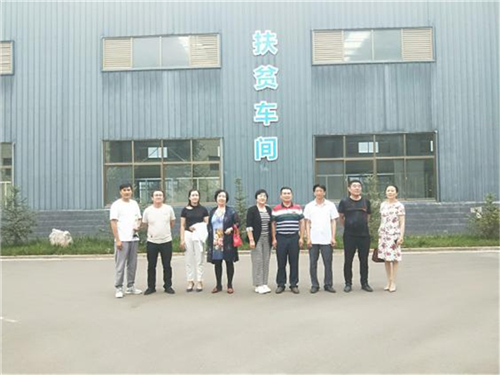1999年7月4日,第24批援苏丹医疗队,告别亲人、离开祖国整装出发。一附院有杨志尚、王月玲、姚美丽、李瑞祥、盖毅文、张少强、刘思伟7名援外队员。

出发当天雨下的很大,科室的领导和同事冒雨去火车站相送。
在北京简短的外交培训后34名队员乘机飞往新疆,从乌鲁木齐出境飞往中转地阿联酋沙迦。很多队员和我一样是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中途到达阿联酋的沙迦,我们首次踏上异国的土地,在波斯湾的海水里游泳嬉戏。
短暂停留后又从迪拜转机飞往目的地。7月10日飞机降落在苏丹首都喀土穆机场,首先体验到的是喀土穆的滚滚热浪。喀土穆是青白尼罗河交汇之处,河流将这座城市分成喀土穆、恩图曼和北喀土穆三部分,类似中国的武汉三镇。苏丹北部位于撒哈拉以南的半沙漠地区,年降水很少,天气预报报告的气温常接近50℃,被称为“世界火炉”。
生活上的艰苦早在我们预料之中,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一些。来到苏丹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专家,都需要能独当一面,能代表中国专家的水平。也许在国内我们这些主治医师还需要在上级医生的带领下才能开展一些业务,而在这里在各自的专业我们都是老大,要带着当地医生(有些年龄比我们大很多)开展工作。当年我33岁。
初次上班遇到的困难很多,首先是语言关,当地医生有些是国外留学回来的,英语基本可以,但口音很重,开始很难适应。但多数情况下是当地的护士跟着我们上门诊,跟我的护士是个男的,叫默罕默德,英语比较差,两年一直跟着我出门诊、安排和准备手术。苏丹病人基本不会讲英语。我们就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加上出国前培训几周的基础,很快就可以用简单的阿拉伯语进行交流,这时候护士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病人说的一大堆话语精炼成简单的、我们可以听懂的阿语。就这样几个月下来我们几乎不需要护士翻译就可以接诊病人。
苏丹医疗条件非常落后,大多数患者经济条件也很差,很多疾病被拖到很严重才来就诊。有时候让患者去拍片子,可能半年后患者才能凑够钱去拍这个片子。而且当年整个国家只有一台CT,对有些疾病的诊断几乎是很困难的。但是一附院的几名队员想着我们代表的是中国,绝不能给中国丢脸。有些疑难疾病也是白天看了,晚上回去再看书、翻资料。当时那里没有网络,要想查资料、看文献是几乎不可能的。
医疗队里队员来自不同的单位,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整个医疗队数杨志尚的英语最棒,甚至有时候专业翻译也邀请他帮忙。有一次来了一个内科患者,患者几乎昏迷,由于内科医生和患者家属交流有困难,一时诊断不清。他们请来队里的专职翻译依然搞不定,只好请杨志尚出马。虽然杨教授的英语带着强烈的陕西方言味道,但他三言两语就问清了病史,正确诊断和处理了病人。这些不光是他流利的英语水平,还有渊博的专业知识。还有一次一个骨科患者来就诊,患者上肢活动有困难。但来自基层医院的骨科队员竟没诊断清楚,让患者去拍片。正好杨教授路过门诊,看到此患者,也是三言两语就诊断患者是肩关节脱位。只见他拽着患者的手臂,脚蹬患者腋窝轻轻一拽患者就好了。
杨志尚是以体外碎石专业的身份去苏丹的,有一次当地医生做子宫切除术,感觉好像损伤了输尿管,马上求助中国泌尿外科专家。泌尿科派去的队员也是个年轻主治医生,手术台上半天也解决不了问题,只好请杨教授去帮忙。杨教授上了手术台,几下就解剖出了输尿管,输尿管并未损伤。他又三下两下帮黑人医生切除了子宫,在场的各科医生和护士看得目瞪口呆,对杨教授佩服的五体投地。当即请示院长要求杨教授每周做一次手术,从此杨教授在医疗队既是碎石专家又是泌尿外科专家。
医疗队总共有三个普外科队员,李瑞祥年龄最小、职称最低,但他的业务水平绝对代表的是一附院的水平。大小手术都是他主刀,其他两位来自基层医院的高年资队员对他也无比佩服,甘当他的助手。胰十二指肠切除在国内也算是高难度手术,一般都是副高以上的医师才能完成。年轻的李瑞祥在苏丹及其艰苦的条件下知难而上,历时8小时完成了苏丹恩图曼医院首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经过他的精心处理患者顺利康复出院,出院后患者还邀请一附院的专家去家里做客,表达对中国医生的谢意。
耳鼻喉科在当地的病种比较复杂,专科设备和手术器械又十分简陋。我当时只是个年轻的主治医师,面对数量众多需要救治的病人,就通过改良器械、自制碘仿纱条等手段开展了整个医疗队数量最多、种类最多的手术。当地人以前几乎所有的手术都需要全麻,但全麻设施比较落后,麻醉意外较多。我就带领当地医生开展局麻手术,开始当地医生和患者对局麻手术有些排斥,慢慢他们逐渐接受。有些医院的职工、熟人还专门来找我局麻手术。

有一天一个年近70岁的喉癌患者来到医院,他跑遍了喀土穆所有的医院都做不了这手术,最后来中国医院(当地人称恩图曼友谊医院为中国医院)求助中国专家。我仔细查看了病人,认为手术可以进行,但医院有些设施不完善,不能保证手术的安全性。患者是当地的富人,愿意提供有些设施。后来在我和患者及家属的共同努力下,顺利为患者做了全喉切除手术,这也是援苏丹医疗队首例全喉切除术。患者家属直夸doctor 虽尼,呆玛穆(中国医生真厉害)。

还有一次我和刘思伟医生在大街上碰到一个患者,面部巨大肿瘤遮住了半个脸和眼睛。我们上前询问了患者,他是因为经济困难一直未能手术。我建议他去中国医院就诊,并向院长打报告建议免费给该患者进行手术,经院长同意减免部分费用。在眼科刘思伟医生和麻醉科盖毅文医生的帮助下,我们顺利切除了肿瘤,使患者恢复了容貌。原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来自眶内的血管瘤,在当地极其简陋的医疗条件下完成这样的手术,难度可想而知。
眼科的刘思伟主治医师是整个医疗队最年轻的,而苏丹的白内障又是高发疾病。刘大夫每周要开展十余例白内障摘除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由于当地没有超声乳化,刘大夫就不断改进手术切口,尽可能使手术微创化。苏丹人无菌意识较差、手术室和手术条件十分简陋,在这种情况下刘思伟的眼科手术无一例发生眼内炎,当地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麻醉科盖毅文可谓当地红人,黑人医生和护士都很喜欢他。苏丹人大小手术几乎都是全麻,他指导黑人开展阻滞麻醉,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尽可能创造条件配合外科医生。苏丹医护人员的无菌意识非常淡漠,打针、输液几乎不消毒,盖毅文就不断指导和强化黑人医护人员的人无菌观念。
除了医疗工作,在两年远离祖国、远离亲人的日子,业余时间有时是很难打发的。当地没有网络、全队只有一台电脑,给家里打电话每分钟15元(那时工资并不高),给家里寄信要一周多才能收到。一附院的几位医生就在这两年里结下了深厚的兄弟般的友谊,他们一起散步、一起钓鱼、一起玩耍、一起学英语,相互照顾、情同手足。他们带头在驻地的空地开荒种菜,经过他们的努力劳作,地里长出了青菜、韭菜、豇豆、冬瓜、西葫芦等,不但改善了伙食还增加了生活的情趣。可惜当时还没有数码相机,许多珍贵的资料没有留下影像。傻瓜胶片相机只记录了两年的部分工作和生活的场景。


转眼已经整整20年了,一附院24批苏丹医疗队的五位男队员依然团结的如亲兄弟一般。医院里人们亲切的称他们为“苏丹帮”,这可能在整个陕西援外史上是少有的。两年的援外生涯,可能失去了很多,但收获的是经历,更重要的是友谊。
编 辑:王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