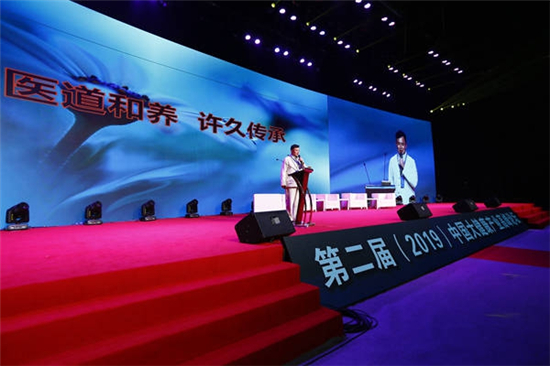李贽作为晚明时期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不论是其性格,其疏狂的行为,亦或是其独树一帜的文学观点,都在当时的文学界形成了一股轩然大波,喜之者视为标杆,不喜者弃为末流,评价泾;渭分明。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并未为李赞列传,可见他没将李贽划归于儒学一派,而是将李贽划为“狂禅”,耿定向因为“于佛半信半不信”亦不能压服李贽,这种将李贽划归于佛门,脱离正统学说的评价,几乎将李贽从学术界剔除出去了。又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王夫之等,对李贽评价非常低,顾炎武曾评价李贽:“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甚至说其“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至于有“败坏天下”之嫌。王夫之则言“合佛老以溷圣道,尤其淫而无纪者也”,评价可谓相当低。

与顾炎武、黄宗羲等相对,钱谦益则对李贽评价非常高,称其“风骨棱棱,中燠外冷,参求理乘,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语皆刀剑上事。”不仅言其行为特立独行,风骨卓然,且赞李贽之观点透彻明晰,往往能一针见血,对其倍加称赞。
李贽非常注重于对人的关注,这一点无论是其在争论中表达的观点,还是体现在文学思想上,都有明显的表现。人的思想与感情才是李赞关注的重点,文章是作为表达人的“情”的载体,而人的“才”、“胆”、“识”则直接关系到文章“情”行发的方式与能力。故而李贽的文学评论观,总体而言,应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是文章之中所流露出的“情”,其二则是作为“情”主体的人的“才”、“胆”、“识”。
当作者有了“才”、“胆”、“识”,却并未将“情”真实而毫无阻碍的表达出来时,则被李贽划归为“画工”这一说,并非李贽不赞同在这一类地方用功,而是这一类的评价标准是一个隐藏条件,只有在“画工”达到一定水准之后,又自然而然流露出了“情”,才能达到李贽的“化工”标准。才、胆、识——重“德”的评判标准
李贽将文章作为“情”的载体,而创作的主体,则无疑是这个“情”产生的根源,故李赞非常注重对于人这个个体的评价,并认为,人的“真性”与文章的“真情”具有天生的紧密联系。若是要看李贽对于文学的审美,首先得分析李赞对于“人”的评价。
除去“绝假纯真”这一条文学思想的核心之外,李贽在文学评判的标准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即作者之“德”,作者的德行是李赞评判此人文章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在《初潭集序》中,李贽云:“有德行而后有言语,非德行则言语不成矣;有德行而后有政事、文学,非德行则政事、文学亦不成矣。是德行者,虚位也;言语、政事、文学者,实施也。”故在李贽看来,德行是文学的基础,同时亦会在文学中表现出来。就如李贽推崇苏拭,唐宋散文不乏大家,但让李贽如此推崇苏拭的原因,是李贽从作品的浩大中品味出苏拭的“德”,在李贽看来,只有德与文相辅相成,才能成就苏試这一大家,如《复焦弱侯》一篇,李贽言道:李贽《初潭集序》见《李贽文集》张建业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硕士学位论文“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祗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馀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文章能垂世不朽者。”
当“德”与“情”被李贽转化为“真”在文章之中的体现,那么作者的“德”也成了李贽考量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指标,只有当作者表现出了足够的“德”,才有基础在文章中表现出最真实的“情”。
当“德”反映在文学思想与文学评论上时,“真”表现在文中,自然而然的会体现在“道德”与“真情”上,换言之,“德”也是“真”的一种体现。而在李贽的观点里,“德”具体到个体之中,表现出来的即为“识”、“才”与“胆”三个方面。焚书中《二十分识》,则是李贽对于“识”、“才”、“胆”三者的具体阐述。
李贽认为,“识”是“才”、“胆”的先决条件,“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而若是有了“识”,纵使“才”与“胆”稍差一点,亦能用“识”来稍加弥补。故李贽说“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如《焚书》中,李贷评论班固,则说“班氏文儒而耳,只宜依司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论也。立论则不免掺杂别项经史闻见,反成秽物矣。班氏文釆甚美,其于孝武以前人物,尽依司马氏之旧,又甚有见,但不宜更添论赞于后也。何也?论赞须具矿古只眼,非区区文才者所能措也。刘向亦文儒也,然筋骨胜,肝胆胜,人品不同,故见识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虽不能超于文之外,然与固远矣。”

当李贽将“识”理解为“智”,“才”理解为“仁”,“胆”理解为“勇”时,则很好解释李贽对于圣人、英杰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了。“识”、“才”、“胆”是区分圣人、英杰的分水岭,圣人必定“识”“才”、“胆”三者缺一不可,虽“识”可稍微补充“才”与“胆”的不足,但若只有“识”而无“胆”与“才”,亦不能称之为“圣”,英杰或有“才”,或有“胆”,或有“识”,才可生胆,胆亦可发才,这两者在一个人性格的特性中可以相互转化,三者之中,事不成而身死;费讳以才胜而识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死,此可以观英杰作用之大略矣”,李贽将识”、“才”、“胆”三者俱全的人,归为圣人一类,“三者俱全,学道则有三教大圣人在,经世则有吕尚、管夷吾、张子房在。”
“识”是首要条件,而“才”与“胆”则是相辅相成的并列条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胆者,有因胆而发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由此,李贽在评论文学作品时,首先看重的,是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德”。看重文学批评之“德”,与其重“情”并不相矛盾,李贽将这两方面的因素以“真”作为联结条件,内化成了一个整体。注重个性的文学审美
李贽认为,不同的个体,其所具备的“才”、“胆”、“识”三者各不相同,这就造成了不同个体“性各异”的结果。这个观点,从李赞的治国的政治观点中亦能得到佐证。
李贽所主张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之治”,而是“至人之治”,“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种已也。”觉得传统的治人之法是“以有方之治双无方之民也”,是“昧于理”的。“至人之治”的关键在于“因乎人”李赞所坚持的是人必须由利益来驱使,自古圣人所追求的是“无欲”的状态,而李贽所承认的,恰巧就是“欲”,《德业儒臣后论》中亦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家居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如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劝之,比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鲁也决矣。”李贽认为,人是有私欲的,这个私欲并不影响人的“真”,承认人的私欲,就是李贽所认同的“真”的体现,以往圣人以“无欲”为最高境界,而这恰巧就是李贽所认为的“假”的根源。“然则为无私之说者,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壁好听,不管脚跟虚实,无益于事,只乱聪耳,不足采也。”在李贽看来,既然私心也是真心的一部分,那么“无私”之说必然是“画饼之说”,追求“无私”,是要用美名而掩饰真心,无异于“知美名之可好而逐之”,在“治人”的“道”上,是“无益于事”的。
结合李贽所追求的“真”,不难看出,李贽真正反对的是圣人所追求的“无欲”、“无私”的这个行为,并用这个统一准绳来要求“性各异”的人,“夫天下之民物众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条理,则天地亦且不能”不仅是做不到的,更是误国的关键,故李贽认为,国家需要各色的人才,关键在于如何治理,《答耿中丞》中,李贽说“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是故贪财者与之以禄,趋势者与之以爵,强有力者与之以权,能者称事而官,懦者夹持而使。有德者隆之虚位,但取具瞻;高才者处以重人,不问出入。各从所好,个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何其事之易也?是非真能明明德于天下,而坐致天下太平者欤!是非真能不见一丝作为之迹,而自享心逸日休之效者欤!”将个性特异的人,用在适合其个性能力的位置上,自然能够坐享天下太平。

在《又答耿中丞》一篇中,李贽开篇即提到:“心之所欲为者,耳更不必闻与人之言,非不欲闻,自不闻也。若不欲闻,孰若不为。此两者从公决之而已。且世间好事甚多,又安能一一尽为之耶?”④这就可以看出李赞所期望的,自己能够做到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从心所欲,不理会他人所言,故李贽极其看重个性自由且毫无阻滞的发展,这与他所坚持童心说并不矛盾,相反,注重个性发展恰巧是李贽童心说的补注。
这也就是李贽在童心说中所力求的“真”在他人身上的体现,在李贽所谓“真”的观点里,顺其自然而不加掩饰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而这个自然与人之天性,放在对古人的评判标准里,则表现在李贽并不要求一定要是“善”,但他对于不掩饰内心情感与私欲的追求则近乎苟严。在评论人物时,李贽通常持一种力求将人物还原成他本身的原貌与心境的追求,就如同他认为君子平日与普通人并无二致,这是君子心境平淡的一种自然表现,君子并非时时刻刻都要保持着外人对君子某些特质的认定的形象,又如他认为圣人亦有私心,亦要穿衣吃饭,亦有人伦物理一样。
李贷对于“个体”、“个性”的重视,每个人的特性不同,自然不能用统一的准绳来衡量。李货在评点作品时,将作者也纳入到了文学作品评点的体系中,由“性各异”的个体而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自然有不同的特点。李贽在文学审美时,注重对“人”的评价,而这种评价折射在文学作品之中,自然就表现为注重在文学作品之中,体现出来的个性。就如李贽推崇苏拭之文,更大程度上是推崇苏拭其人,《复焦弱侯》则说:“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祗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这大抵亦来源于李赞对于“真”的追求,文章之真情源于作者之真心,作者之真心在于作者之“真人”,真人以真心传真情,则自然能够传神。尚奇的文学审美
李贽看重文章之“情”,是否就意味着他放弃了文章之中的“礼”呢,答案是否定的。如前文分析,尽管李资表现出的是一种不举礼法的狂傲个性,但就内心性格而言,李贽对于礼法的态度可谓已经内化到了一种本能,而这种矛盾表现在文学评论中,李贽在重视作品真情行发的同时,对于作品的“礼”,即文章所该有的体例与格局构架,亦十分看重。并且,李赞认为,“礼”本身也包含在“情”之中。在李贽看来,好的作品结构,往往能够更好的表达出作者的“情”。如《玉合》一篇,李贽评道“此记亦有许多曲折,但当要紧处却缓慢,却泛散,是以未尽其美,然亦不可不谓之不知趣矣”。这是李贽评《昆企奴》中,对于昆公奴一篇的总体构架的评论,在李贽看来,戏曲与小说,当要紧处需紧凑,当缓散处需平稳,节奏拿捏适当,才是“尽其美”,否则若是“当要紧处却缓慢,却泛散”则是“未尽其美”,但同时,李贽也承认这样的处理方式,也并不是一无可取,不同的戏曲小说故事,其要表现的重点不同,于情节轻重缓急的处理方式上,必然也不一样,在李贽看来,作品构架的设计,故事节奏的拿裡把握,为的是突出作品最关键的主题特点来的,《昆企奴》重在突出其“奇”,若太容易就让读者把握到其节奏,反而会失去让读者称“奇”的写作初衷,故李贽说“然亦不可不谓之不知趣矣”。又如《拜月》、《红拂》的点评,李贽开篇即说关目好,曲好,白好等等,这便足以证明李贽并非不注重结构与语言,而是在他的观点里,结构是为故事来服务,而故事是为人物服务,人物是表达“情”的载体,“情”则是化工最关键的点睛之笔,故《琵琶记》在李贽的评价中,得一“画工”评论,因将写作技巧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却恰恰缺少作品之中最富有灵魂气息的“情”。但这并不代表李贽就不承认《琵琶记》画工所达到的高度。又如李贽自己也创作诗歌,并且他对于诗歌的理解,恰恰就认为诗歌的作用是用以泄胸中之闷气,或者对于李贽而言,所有的文体都是用以泄胸中之闷气,行一己之见,发一家之言的媒介,并没有小说、诗歌、戏曲的区别。

但李贽也并非完全不注重诗歌的格律与感情,《读律肤说》中,李赞对于诗歌的格律与格式,也很明确的表达了观点。李贽认为,诗歌“淡则无味,直则无情。宛转有态,则容冶而不雅;沉着可思,则神伤而易弱。欲浅不得,欲深不得。”这是对于诗歌总体的评价,李贽注重诗歌中对于情感的表达,但这个表达也需要有一定的技巧,不能表达过度,亦不能完全无视诗歌的音律与格式,李贽认为“宛转有态”和“沉着可思”这两者若是过度,则容易造成诗歌产生“容冶而不雅”及“神伤而易弱”的缺点,故李贽在诗歌创作中,也很看重一个“度”的把握,无论诗歌是说理或是行情,过度则会妨碍诗歌本身的自然。同样,对于诗歌的格律方面,李赞也非常看重“度”的把握,认为“拘于律”者则被格律所制而成为诗奴,使得五音不克谐,“不受律”则不成律,而成为诗魔,使得五音相夺伦。而这个度,在李赞的观点里,则认为是诗歌的“自然”。
李贽认为,声色源于情性,情之所至,则诗歌便自然了,而诗歌自然了,于是格律与感情也就水到渠成了。但过分的自然,又有不注重格律之嫌,故李贽又言“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在李贽的观点中,礼义本来就包含在情性之中,也是“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并非有了礼义,遵从格律就是不自然的,自然的情性是建立在礼义基础之上的,在诗歌中,也就是建立在格律之上的。所以李贽才会有了最末段“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的总结。虽然诗歌的格律有统一的标准,但写作者的性格的不同又会造成诗歌格调的不同,故李赞又说:“故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矿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