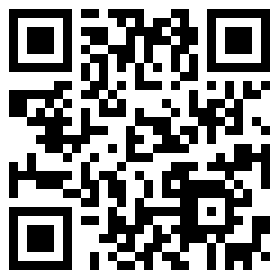提到赵廷隐,你也许会感到陌生,但是提到成都博物馆的这件文物——“撞脸”国乒老将马龙的陶俑,你一定不陌生。这件文物正是出土于成都龙泉驿区赵廷隐墓。这位神秘墓主人在五代时期的成都赫赫有名,要知道,他可是打下后蜀江山的开国功臣。不过,考古人员在这样一位战将的墓中,却发现了文学与音乐的印记。作为赵廷隐的长子,赵崇祚是《花间集》的编著者,《花间集》是中国第一部文人词集,为后人记载了千年前成都“喧然名都会”的盛况。
五代时期的豪华墓
墓主是后蜀开国大将
2011年,成都文物考古队在龙泉驿区十陵镇发掘出土一座五代时期的大型砖室墓。这是继前蜀王建墓、后蜀孟知祥墓后,四川发现的最好、最大的五代时期墓葬。
这的确是一座五代时期的豪华墓葬。经过一条长20米的墓道,一座高大的砖砌拱形墓门出现在眼前。墓门上依稀可见精美的卷云、草叶状彩绘纹饰。穿过墓门便进入一个270平方米的墓葬主体,在长15米、宽18米的大型墓室中,内壁全部着彩绘壁画。考古队员在发掘赵廷隐墓过程中,发现墓室墙壁上的卷云、草叶、凤鸟、人物等装饰性画面,有的还能辨认出从前的模样。墓室为“三室一厅”格局,一主室列主人棺木,两耳室加一后室陈列着大量神态各异的随葬品。墓室中央是一座长约7米、宽约3米的棺台。棺床南北向放置,上部由石板铺成,下部由砖砌成。木质棺因年久已腐烂,只剩下棺台。

当时,人们一度以为这是王建儿子的墓葬,最终确认墓主为后蜀宋王赵廷隐的关键证据是墓志铭。在主室与雨道台阶处,考古人员发现了1米长宽的墓志。墓志已损但基本完整,其上阴刻近3000字,记录了赵廷隐家族谱系、一生经历、重大战役及子嗣情况等信息。历史上,赵廷隐是一位显赫的人物,《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九国志》《十国春秋》《资治通鉴》等史籍上对赵廷隐皆有记载,《九国志》对赵廷隐及其次子赵崇韬甚至单独立传。
后唐时,赵廷隐随孟知祥入西川,作为其手下得力大将,为孟知祥开疆辟土,打下后蜀江山,成为开国元勋。后蜀建立后,赵廷隐更位列三公,官至太尉,地位极高。透过墓志铭可得知,赵廷隐有3位夫人、3个儿子和7个女儿,其中,长子赵崇祚就是《花间集》的编著者。
蜀地物阜民丰
诞生中国第一部文人词集
诗言志,词言情。词作者更多通过写词来抒发男女间的悲欢离合之情。前后蜀时期,蜀中相对安宁,成都平原具有都江堰水利之惠,蜀地物阜民丰,“俗不愁苦”“无凶年忧”,蜀纸和雕版印刷闻名遐迩。这些都为《花间集》的问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花间集》诞生在成都也因此有了历史必然性。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以言情为主的词文学很快就为成都文化人所接受,成都词文学之盛远超全国各大城市。此一时期,成都的词文学“雅正之作,日趋减少”,而“浓丽小词,蔚为大观”,逐渐形成了词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花间词派”。

广政三年(公元940年),赵廷隐的长子赵崇祚所编的《花间集》问世。《花间集》是中国第一部文人词集,收录了18名作者的词作500首。花前月下、男女之情的占十之七八,其余为咏史征伐、行旅写景之作。入选作品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而入选作者并不局限于西蜀境内,《花间集》展示和总结了当时词坛的总体面貌。其中,除温庭筠、和凝、皇甫松三位外,其余15人皆是活跃于成都地区的官宦士人,包括前蜀宰相韦庄等,其中还有后主孟昶的宠妃花蕊夫人。
《花间集》中,18位作者的词作风格多变,或婉约绮丽,或华美艳丽,或清淡明秀,或意境深远。温庭筠是“花间词派”中写词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词人,他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则被视为经典。
“花间词派”在唐宋之际另成一派,风格独特,极大地丰富了晚唐五代时期的成都词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过,赵崇祚当时的头衔是“银青光禄大夫行卫尉少卿”。一名武将为何“跨界”,“广会众宾,时延佳论”编纂词集,甚至能请来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欧阳炯作序?赵氏家族其实用心良苦。

后主孟昶崇尚道教,好舞文弄墨,能分韵赋诗。《花间集》语言风格艳丽精美,所选词曲很多都有道教色彩。赵崇祚以此投孟昶所好,以此来巩固赵氏家族利益。《花间集》虽是赵氏家族为了讨好孟昶而编纂,但客观上对宋词的繁荣开风气之先,被誉为“填词家应遵之格”,其香软柔媚的内容和绮丽曼艳的风格,开了婉约派先河。其词风直接影响了北宋词坛,直到清代的“常州词派”也深受其影响。
20余件伎乐俑出土
印证成都音乐文化繁荣
在成都博物馆里,有一组由20余件五代时期精致华丽的伎乐俑组成的宫廷乐队,十分引人关注。这组伎乐俑出土于成都龙泉驿的五代赵廷隐墓,看个体,形态各异、面目含笑;看整体,彼此呼应、气势非凡。这些伎乐陶俑被放置在独立展柜中,如同一支乐队演奏现场般惟妙惟肖。
回溯到文物出土之时,最让考古界惊叹的就是这一整支歌舞乐队。20余件伎乐俑高约0.6米,皆为立姿,按装束及姿态分为乐俑、歌俑及舞俑三种。其所着服装鲜艳富丽,衫、裙清晰可辨,且多描金。乐俑所执乐器有琵琶、羌鼓、齐鼓、笙、排萧等。歌俑神态尊贵,头饰金簪。舞俑中两件为柔舞俑,着女装,姿态柔和优美;一件为健舞俑,着男装,姿态刚健有力。这是迄今西南地区发现的最精美伎乐俑组合,且其中部分俑所着服饰具有典型的异域风格,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五代女性服饰、五代音乐史的宝贵材料,还原了成都五代时“喧然名都会”的盛况。

五代时期,成都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经济文化优势,不仅通过蜀道将中原音乐文化、西域音乐文化带到蜀地,并沿南方丝绸之路将其传播至域外诸方,而且成为南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北进中原与南、北丝绸之路多元音乐文化交融、发展的枢纽。此时的成都,不仅保存了唐代音乐文化(尤其是宫廷歌舞音乐)的精髓,更为宋代音乐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成为唐宋音乐文化连接的纽带,在中国音乐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这支庞大的歌舞乐队出现在赵廷隐墓中,自然是其生前生活的一种写照,也印证了《花间集》的流行。虽然无从考证这支乐队演出的曲目,但《花间集》是当时教坊中歌唱之人的歌唱选本,广受欢迎。“花间词”作为“以资羽盖之欢,用助妖娆之态”的应歌之作,自然需要歌伎演绎,当年像赵廷隐这样的王侯将相家中,都养了庞大的歌舞乐队。花蕊夫人即为歌伎出身,她的《宫词》多次描写了宫廷的歌舞升平,“离宫别院绕宫城,金版轻敲合风笙。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长有按歌声。”优美的歌声、婀娜的舞姿,使词这一全新的艺术形式迅速风靡。从王建墓的“二十四伎乐”到赵廷隐墓伎乐俑,为人们勾勒出成都从前蜀到后蜀的音乐繁华景象。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李雪艳 供图 成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