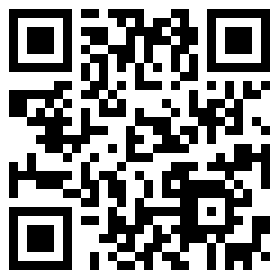“文学上海”,在百年海派文学中被不断书写,其中尤以张爱玲、白先勇以及王安忆为代表。三者笔下呈现的“文学上海”异中有同,均以上海这座以时间构形的城市为依托,在城市与文学的关系中,描绘出上海这座现代城市在历史时间及文化记忆中的诸种面相。因此,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上,我们应该保持更加多元的取向,对那种以牺牲记忆来谋求发展、以单一的现代时间来规约上海发展的做法保持一定的警醒。
原文 :《海派文学中的上海时间》
作者 |上海大学文学院 邓金明
图片 |网络
张爱玲:历史就在生活中
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张爱玲的时间感是非常突出的。一方面,她有着明确的时间观或时间意识;另一方面,她的写作体现出强烈的时间特色,有着很强的记忆痕迹,以至于形成一种“记忆的艺术”。而从更深处而言,张爱玲的时间观及其写作的时间特色与上海这座城市又是分不开的。
张爱玲的时间观,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对“记忆”、“时代”、“传统”以及“历史”等几个核心概念的理解上。张爱玲认为历史是日常的。张爱玲的日常生活史观,迥异于左翼史家注重政治经济变革和革命斗争等重大社会问题的政治经济史观。她的文章很少谈及重大历史,倒是有不少谈服饰、饮食变迁等属于文化生活史的内容。她具有一种从日常生活来观察历史的眼光,认为历史就在生活中,在生活中被不断重复、实践着,“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着活跃的演出”;而且认为“历史”是“没有系统的”,没有什么“完整性”,这也是基于历史的日常琐碎性。最后,张爱玲认为历史是记忆性的。记忆是一种不改变历史线性时间进程的回溯策略。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论中,记忆并不显得重要,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进化论中,记忆同样也不重要,惟有在历史退化论中,记忆才显得尤为重要。记忆是处在时间流逝、历史堕落之中唯一的自救办法。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是日常的,而日常性的回溯方法只能是记忆,它不同于典籍史册的系统性记录,而是零散地、不自觉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在《更衣记》中,张爱玲甚至将历史变迁融入到日常的季节换衣、气味记忆中来。当然,强调历史的记忆性,也意味着强调历史的细节性。保持在新旧文化之间、传统与现代杂糅的生活状态之中,正是张爱玲对自己写作和处世的定位。张爱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她看到了上海这个“摩登”城市,仍然保持着对传统、对旧文化的记忆,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它。

由于张爱玲对现代性的来临一直怀着隐隐约约的恐惧感.及时行乐的世纪末情绪与古老家族衰败的隐喻贯穿了她全部的个人记忆,一方面是对物质欲望疯狂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对享乐的稍纵即逝的恐惧,正是沦陷区都市居民沉醉于“好花不常开”的肺腑之痛,被张爱玲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给以深刻的表现。如果说,这种都市民间文化的基本面是“好花不常开”、“及时行乐”等末世情结的话,那需要追问的是,这种末世、乱世情结是传统文化性的还是现实社会历史性的?或者我们可进一步追问,这种“不安”、“恐惧感”是否根植于动荡的现代都市本身?而传统文化记忆又是如何融入到现代都市体验中去的?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白先勇:“最后的一抹繁华”
白先勇早年生活过的大陆城市有桂林、上海、南京、北京,但是唯有上海,白先勇认为是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记的大陆城市,也是作品中始终留存的影子”。“时间的流逝”作为白先勇一切作品共有的主题,并不是抽空的、形而上的,而是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与上海在中国现代政治、社会、文化中的历史变迁有着紧密的关系。一方面,从延安时期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到新时期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讲究个性与尊严的贵族与贵族艺术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洗礼下早已风消云散、荡然无存了;另一方面,在当代,随着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以及大众文化的大行其道,讲究特立独行和精神尊严的“贵族气”,也注定无法避免其陨落的命运。与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上海如今正毅然决然大步走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被历史进程所抛弃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仍然是一个难题。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记忆”而不是“历史”,因为各种档案文献、史书方志并不能代替面对过往时间时所产生的种种感受,这也是白先勇一再强调的“沧桑感”,“这几十年,我们国家和民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是过几十年再来看这段历史,就会有各种感触,叫沧桑感也好,叫美好的回忆,或无穷的怀念,都行。好的作品,它给人的启迪,它所引起的回味,决不是一两句话所能概括的”。可在当代中国(上海尤为典型),恰恰是以历史代替历史记忆,以冷冰冰的文献档案代替时间过往所引起的人的丰富感受。历史被无情地科学化、数字化和图表化,而欠缺的却是人性化、人情化,而这也正是在当下各种“城市记忆工程”建设中屡见不鲜的问题。

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
跟张爱玲一样,王安忆也关注日常世俗,但她的关注带有更多平民的、感同身受的味道。更重要的是,王安忆经历了共和国历史下的上海,这使得她能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和更后撒的时间点来看待上海的城与人。正因为这种关注点的亲近与时间点的后撤,使得王安忆能拥有更为复杂的时间意识。
在王安忆的“文学上海”中,时间的并置性与各种不同性质的时间杂糅在一起。由于历史的急速进程,历史发展中的时间并不是均质的。有资产阶级的时间,也有无产阶级的时间;有舒缓的时间,也有紧迫的时间;有顾后的时间,也有瞻前的时间。正如张旭东指出的:“呈现在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是一个在时间状态上非常多样化的上海。具体地说,它不是物理空间中凝聚着的无时间状态的城市。它并未因1949年带来的转变而沉于怀旧,一味梦想过去;也并未因1990年代以后的发展而忽然在国际化空间中重新找到自我。事实上,百年上海的历史都一层一层地积淀在这个城市空间中,积淀在一些极为具体的日常空间里。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以及不同阶级在文化上的符号、不同阶级的记忆、具体生活的仪式等,在上海这个城市的日常空间中,都是活生生的东西,任何一方面都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比如,无产阶级以为自己把资产阶级消灭了,但事实上资产阶级不但幸存下来,而且还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里生活得很好,占据着自己巨大的所谓的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特权’”。

在中国所有城市中,上海是时间最为错综杂糅的一个。上海之为“上海”,“并不在于它更新、更先进、更革命、更有大都市意识,而在于它能更集中、更典型、更有代表性地展现新与旧、先进与落后、革命与保守、现代与传统之间复杂的纠葛关系”。王安忆所书写的“文学上海”绝不是“怀旧”,她在“文学上海”里所记取的,是在历史变迁中各种时间的交锋、碰撞、鼎盛及衰亡的全景。
(本文属“上海市高等教育内涵建设‘085’工程:都市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325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社会科学报
做优质的思想产品
www.shekeba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