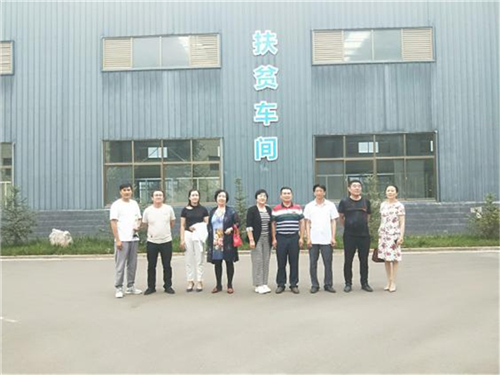张爱玲是现代中国佩代文坛的一颗彗星。
她的奇言独行,令人侧目,但她的一枝生花妙笔,正如胡兰成所言,是千娇百媚。
她的陨落,有如将星坠地,锵然有声。

张爱玲是一位天生的作家,她的作品确立了她在文学界的地位。但少有人知,为了生计,张爱玲还曾当过翻译,而她所留下来的翻译作品,都具有独特的审美情趣。
如张爱玲所言:实在没办法,就算是牙医的书,也要译下去。
一、刻意练习,英汉随意转换
张爱玲从小接受私塾教育,才华横溢。她的母亲黄逸梵曾出国留学,并决意用欧美教育模式培养女儿,因此,张爱玲的英文非常好。

中学时,张爱玲就读于圣玛利亚女校。这所学校,是当时有名的贵族学校,课本主要使用英文版本,任教的老师也多为英美籍。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道:“她的英文比中文好,随便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
后来,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学习了三年。这三年间,她并不急于创作,反而努力锤炼英文表达能力。因为刻意训练,原本只能读英文的张爱玲,渐渐达到能够在英汉两种语言间自由转换的境界。
从港大肄业后,张爱玲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不久再次退学。
此后,她开始为《二十世纪》撰稿,同时将其中的散文如《中国人的生活和服装》、《还活着》等改写为中文,收入《流言》。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改写,通常指的是,由深谙中英文的译者一人担当,译者存有较大自由度,是典型的“一文二作”。
这种改写,对译者的文学素养要求非常高,是典型的再创造的结晶。
《女装·女色》、《浪子与善女人》,这些都是张爱玲好友写的散文,而张爱玲则将其译为英文,先后发表在《天地》和《杂志》两刊。

与平实通顺的中文相比,张爱玲的英译,老到精炼又有几分俏皮,其间颇多佳句,深受读者好评。
二、张爱玲和《老人与海》
1952年张爱玲抵达香港。当时的香港,人口50万,想靠卖字为生无异于天方夜谭。
为了糊口,她只能替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翻译。
期间,她先后译有海明威《老人与海》、《睡洞的故事》、《鹿苑长春》等。

实事求是地说,张爱玲并不是对以上著作的翻译都投以极大的热忱。正如张爱玲自己坦言:“我对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
张爱玲对少有人间烟火的作品,存有较强地抗阻心理。但是生活的重担,已经让她没有选择的余地。她喜欢海明威,但译另几个人的作品则是“硬着头皮”做的。
她说:“我逼着自己译爱默生,实在是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
而翻译华盛顿·欧文的小说,她更坦言:“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谈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
因为不同的心境,张爱玲翻译出来的外国作品,在质量上呈现较大差异。当然,这种差异并非好与坏的区别,而是巅峰和较好的差别。
张爱玲很喜欢《老人与海》,认同其中罩染着的苍凉色彩和荒诞意味。张爱玲曾言:“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对照。悲剧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三、认真翻译每一部作品
张爱玲是个敬业的人。
当一个翻译者,翻译出了名气以后,常常会请别人代笔,可张爱玲始终坚持自译,甚至是再创作的那种自译。
语言与语言之间,是有差别的。正如中国的古诗词,直译成英文便惨不忍睹。
虽然是迫于生计,可张爱玲依然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

她翻译的作品,是以读者为导向的,用词符合读者的习惯,同时还能准确传达原文的含义。
纵观张爱玲的翻译,她的不少作品,往往根据读者的需要,并用了多种手法。
如她将《海上花》不少部分删去不译,并且在注释中解释,这是为了满足西方读者需要。而在翻译《桂花蒸,阿小悲秋》时,原作约3588字并未翻译,因为其中大多为对西方人的负面描写,会引起读者的不快。

除了略去不译外,增译在张爱玲的翻译中也是频频出现。
如在翻译《桂花蒸,阿小悲秋》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张爱玲增加大量说明介绍阿小的丈夫。在涉及文化差异时,她往往也会在译文中添加说明。
改译,也是张爱玲惯用的翻译手法。
之所以改译,大多也是为了方便读者记住人物,理解人物性格。

当然,这一切与原作有区别,但并未违反作品的忠实性。必要的时候,她也会保留长长的修饰语,哪怕这在英语作品中是少见的。
比起形式上的忠实,张爱玲更重视实际上的忠实。

总而言之,作为一名作家,张爱玲担得起天才之名,作为一名翻译家,她同样算得上传奇。而她悲剧的一生,与她的作品恰是完美合拍的。
这种不完满,构成了张爱玲独一无二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