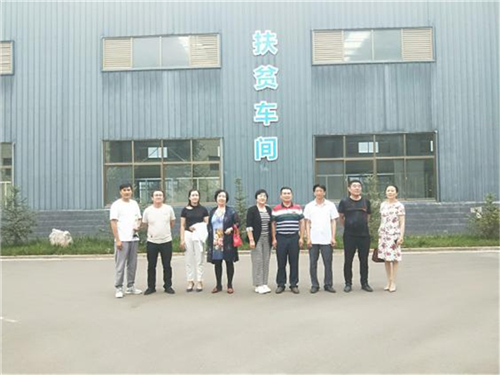铜陵山水之门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么好,也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糟……
自清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首克铜陵,至咸丰十一年八月清军攻陷铜陵,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尽管双方屡有争战,但铜陵基本处于太平军的控制之下,并组建有铜陵县太平天国基层政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黄山书社版《铜陵县志》有载,惜乎纪事简略,且多处与史实相冲突。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后,相关史料几乎为清官方毁尽,但细阅当时文人的相关著述,仍可复原历史情境。
曹蓝田《璞山存稿》中,有多篇叙及铜陵地区太平天国诸事。曹蓝田(1810—1857),字琢之,号璞山,铜陵县人,道光丁酉(1837)举于乡,后选颍上县教谕,客死任上。

太平天国
咸丰二年(1852)腊月,太平军攻陷武昌,檄称东下江宁(今南京),铜陵为必经之地,地方缙绅大为惊恐,曹蓝田举家“避处穷乡”。次年为癸丑科大挑,即从举人中选拔官员,诸亲友鉴于当前时局,且曹蓝田之弟已在京城,家庭需要得力者照顾,皆劝曹蓝田不要离乡。但是,大挑一等将任知县用,二等亦能获得教职,曹蓝田不想放弃,毅然冒险前往京师。
咸丰三年正月十二日,曹蓝田来到铜陵县城,同乡举子朱坦之、俞迓之与其同行。有清一代,安徽省境官方驻军仅有万余,且集中驻于寿春镇。太平军即将入皖,朝迁急调苏、浙、鲁等绿营兵援皖。曹蓝田在县城看见,“浙省援皖兵二千、舟数十,泊县西小矶头”。三天后,曹蓝田乘舟抵达荻港,又见“驻兵二千,席屋数十间卓立风雪中,大炮数尊横卧江岸”。曹蓝田认为,太平军想顺江东不会太容易,铜陵应该是安全的。

太平天国
这一年的大挑,曹蓝田兄弟双双落榜。四月十九日,曹蓝田离京返乡。这时的形势,已大大出乎曹蓝田当初的判断:太平军不仅攻克了江宁,而且已进入皖北地区。曹蓝田顺利还乡都成了问题,更不知家乡被太平军占领后是何情形。不能原道返乡,曹蓝田绕道河南,经由安徽正阳关、霍丘、六安舒城、庐江,于六月十四日抵达铜陵。
家乡景象,完全出乎曹蓝田的预料:太平军占领下的铜陵,社会秩序井然,亲朋故友皆在,曹氏也是“阖家平安”。

太平天国
太平军占领区的情形,为何与官方邸报的描述天差地别呢? 海虞学钓翁《粤氛纪事诗》注载:“贼由九江东下,皖省各处纷传伪诏,官府告示止用短条,不写咸丰年号,称贼为西兵、西骑。甚至绅士胁其令长预造烟户册,欲俟贼至,郊迎三十里,跪而投册纳印者,有门首粘一黄纸顺字者,有箕敛银钱、粮米、食物馈送者。闻有某处馈物甚微,而有生姜、山药并装一桶,用黄纸糊之,贼嘉而受纳。”
海虞学钓翁所记的故事,在清末流传甚广。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甚至将“一桶姜山”杜撰成纪晓岚故事。方宗诚《辅仁录》载:太平军入皖后,“庐州知府胡元伟、六安知州宋培之、铜陵知县孙润、舒城知县学横祷,屈身降贼。”率百姓箪食壶浆以迎,将生姜、山药并装一桶,寓意太平天国“江(姜)山(药)一统(桶)”的,正是铜陵知县孙润,无有其他“屈身降贼”的清方官员。

太平天国
太平军进入铜陵,没有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社会过渡相对平稳,甚至是一派欢乐景象。(清)方江《家园记》载:咸丰三年二月初四日,“贼(太平军)过大通,联三船,张锦帆,女乐侍酒,童子傅粉被锦执旌旆,微飔荡漾,箫管细奏,缓歌而下。”铜陵“知县、翰林孙润归义”,避免了太平天国运动前期铜陵地区的社会动荡。太平天国在安徽组建地方政权,孙润被调往省城安庆,担任太平天国安徽省安庆郡怀宁县监军。据《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湘军攻陷安庆城,孙润被湘军俘杀。
孙润归义,很大程度上是迫于铜陵城防薄弱,同时也是顺应铜陵缙绅及平民的诉求。在曹蓝田返回家乡铜陵之前,太平军已再度由江苏入皖,以肃清皖江沿线清军残余。咸丰三年9月26日,翼王石达率部进驻安庆,辟清安徽巡抚衙门为翼王府,布告安民,首开天朝地方政权建设,调整天朝制度,史称“安庆易制”。

太平天国
安庆易制,涉及太平天国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重大政策转变,改“贡献制”为“照旧交粮纳税”,改禁止工商私营为鼓励工商私营,改普征兵制为招募入伍。太平天国早期的《待百姓条例》及《天朝田亩制度》等,既遭清廷污化,亦引当代学界争议,但在铜陵地区并未施行。在地方政权建设上,天朝组建了省、郡(府)、县三级地方政权,铜陵地区为天朝安徽省池州郡铜陵县,县下设有各级乡官。
铜陵县被太平军占领后,清官方机构均远离了县城,成为“流亡政府”。咸丰三年秋,太平军在铜陵发布安民告示,通过乡官招抚流亡、清查户口、维持治安等。铜陵百姓的拥护与支持,太平军的地方政权建设十分顺利,曹蓝田在《与邓太守书》中,将之归于“奸民从中煽惑,愚民随声附和”,以致很短的时间内,太平军在铜陵的统治“遂成牢不可破之势”。咸丰四年春,“奸民(铜陵百姓)迎伪官(太平天国官员)及贼党(太平军)百余来踞县城”,太平天国铜陵县地方各级政权全部建立。

太平天国
咸丰四年八月初一日,太平天国铜陵乡官在县境开始征收钱米。这种税赋征收方式,与清朝并无多大的不同。唯一的差别,是太平天国直接向土地使用者征收,而不是面向土地所有者,天朝以此切断佃户与地主之间的联系。除极个别缙绅因顾忌而反对外,绝大多数平民都积极配合。
曹蓝田的立场,则始终与太平军相对立。这种对立,曹蓝田自认为是出于感念“朝廷培养之恩”,其实是对自身既得利益的维护。曹蓝田之父是铜陵知名的秀才,其兄弟二人同为举人,连同其侄曹荣绶、曹荣黻在内,曹氏家族此时至少有五人拥有功名,这在铜陵非常罕见。与平民及普通缙绅不同,曹氏家族一旦归顺太平天国政权,意味着数代人的努力付诸东流。而曹氏家族坚持与太平军为敌,也确实能获得朝廷厚遇:曹蓝田最终实授教谕、署知县,衔六品;曹荣绶与曹荣黻,亦为朝廷所用。

太平天国
安庆易制前,太平军一度采用“纳贡”制,即由地方耆老出面征收财物。咸丰三年十二月,太平军前往顺安镇征收钱米,曹蓝田秘密召集地方亡命,试图截杀。曹蓝田给亡命之徒开出的条件是:“共攻毙贼,均分其赀”。但是,曹蓝田的做法并无正义,且风险极大,因而不为地方其他缙绅所认可,最终“以诸父老苦劝而止”。
在《拒诸亲友劝输粟书》中,曹蓝田坦陈铜陵拥护太平军者之众:“顷见他人相率输将”。但曹蓝田坚持与太平军为敌,拒绝向乡官缴纳钱粮。针对曹蓝田的抗拒行为,太平天国政权并未采取过激措施,而是动员其亲友予以规劝。面对亲友的劝说,曹蓝田无言以对,最终给亲友留一封信,慨叹朝廷“计恩甚厚,一旦反颜,于心何忍”,无可奈何地离开家乡,直到去世。

太平天国
在太平军统治的八年里,铜陵百姓安居乐业,地方鲜见战事发生。见诸《安徽通志稿》的战事,仅有两次:“咸丰五年八月壬辰日,清军收复铜陵”;“咸丰六年正月戊辰,清军再收复铜陵”。这两次战争,规模较小,对平民影响不大,且时间很短,最短的一次清军只占领铜陵六天。铜陵地区的社会状态,在英国人呤唎的著述中格外清晰。
1860年仲夏,呤唎自上海前往武汉,途经铜陵时逗留了三天。在这三天里,呤唎上岸旅游、射猎,在大通附近与平民交谈,还让水手带回山上的泉水。铜陵的自然风光与社会景象,给呤唎留下了美好印象,多年之后,他仍回忆说:“我经常怀念着那冰凉的山泉,那罗曼谛克的溪谷。”

清军与太平天国军交战图
太平天国治下的铜陵,呤唎的记载与曹蓝田有天壤之别。呤唎在《天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写到:“大通附近的村庄似乎很穷苦,太平军或清军时来此地,这对于村民来说自然是不幸的。我们虽然知道有纪律的饥饿的军队在敌人国内是什么情况,但是却很少认识到无纪律的中国官军的光景。这里的房屋并未遭到破坏,唯一被太平军毁坏的只有一座大佛寺,照例每块砖头都被砸成堆粉碎,留下一堆瓦砾。人民谈到清军来此的情况,都是咬牙切齿。他们说,清军奸淫妇女,杀戮保护妻女的男子。他们又告诉我,太平军待他们很好,只叫他们捐输粮食;有个太平军对一个姑娘强暴,就被杀头,他们把枭首示众的地方指给我看。他们十分欣然地讲到,太平军首领英王不许兵士拿人民的东西不付钱。”
呤唎并没有回避太平军对铜陵的破坏,但这种行为实出自宗教信仰上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呤唎与曹蓝田不同的记载,有着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呤唎对太平天国革命怀有同情,曹蓝田则对此深刻仇视,二人观点与视角差异,并不妨碍真相钩沉。

曾国藩连环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