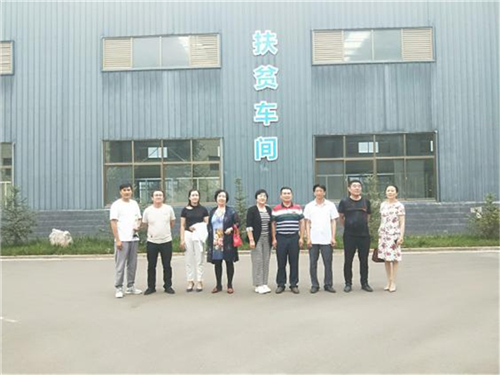赵孟頫和鲜于枢,无疑应该是元代最杰出的书家中的两位。而赵氏三十多岁时为鲜于枢书其父《鲜于府君(光祖)墓志》,不仅为其早年书法,尤其是小楷碑版的典型力作,更是研究鲜于枢家世生平,乃至赵氏与鲜于枢交谊的重要文献。且现知仅有二件原拓存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北大本”)拓虽较早,惜有残缺;故上海图书馆所藏(以下简称“上图本”),遂成唯一全本。前者曾经缩小影印,收入文物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后者也作为“翰墨瑰宝:上海图书馆藏珍本碑帖丛刊”第二辑五种之一,2012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原色精印。

北大本《鲜于府君墓志》

上图本《鲜于府君墓志》
正如近世学者柯昌泗在其《语石异同评》 (《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4月)中指出的那样:“宋元碑于文史之用最钜”,由元代著名文人周砥撰文的《鲜于府君墓志》,因记鲜于枢家族世系及其曾祖、祖父事略,更详鲜于枢之父鲜于光祖(子初)生平行迹,而极为有关研究者所注目,屡加引述。更重要的是,该志后附刻盛彪题记中,有“太常公既志鲜于府君之墓,未及卜兆而公卒。后十七年,当大德戊戌,府君之嗣枢,始得吉于钱塘县西次孤山之原……其嗣枢年五十有三”诸语,由此,鲜于枢的确切生年为南宋淳祐六年(1246),终得推定,从而解决了鲜于枢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基础问题。
赵孟頫年轻时与鲜于枢初识之下,即一见倾心,结下友谊,并至终身。赵氏《松雪斋文集》中多有关涉两人交往之篇什,其中《哀鲜于伯几》长诗所述,似最详备:
生别有再逢,死别终古隔。君死已五年,追痛犹一日。我生大江南,君长淮水北。忆昨闻令名,官舍始相识。我方二十余,君发黑如漆。契合无间言,一见同宿昔。春游每挐舟,夜坐常促席……奇文既同赏,疑义或共析……刻意学古书,池水欲尽黑。书记往来间,彼此各有得。我时学钟法,写君先墓石。江南君所乐,地气苦下湿。安知从事衫,竟卒奉常职。至今屏障间,不忍睹遗墨。凄凉方井路,松竹荫真宅。乾坤清气少,人物世罕觌。绯袍俨画像,对之泪沾臆。宇宙一何悠,悲酸岂终极。
因此,鲜于枢以父亲墓铭书丹这样的要事,郑重请托,决非仅仅因为赵氏擅书;而赵孟頫时虽年轻,却以精楷小字尽心报命,也正缘于非同寻常的情谊。故清代王良常(澍)跋语中称其“文外有笔,字中有韵,为吴兴楷书之冠”,洵为真赏知音。而赵氏一生中,除为鲜于枢父亲书写墓志之外,又曾为书法史上与鲜于枢齐名的另一元代书家康里巙巙之父撰写神道碑铭,亦可谓难得佳话。
赵氏三十六岁(1289)所书《姜夔兰亭考》卷后自题中,已有“予自少小,爱作小字;迩来宦游,无复有意兹事”之语,知其早在少年时代,就喜欢写小楷。则其所用之功,当尤勤且深。五十六岁(1309)时重题此卷,又忆及二十年前其“为郎兵曹”,即《鲜于府君墓志》前题衔“奉训大夫兵部郎中”时作书的用功趣向:“余往时作小楷,规模钟元常、萧子云。”今观其三十四岁(1287)所跋《孝女曹娥诔》、传王羲之《大道帖》,以及三十六岁(1289)题钱选《八花图》卷,乃至三十八岁(1291)所书小楷《过秦论》诸迹,皆楚楚有致,古趣盎然。而作为“我时学钟法,写君先墓石”的《鲜于府君墓志》,小楷规整,气息典雅,多有魏晋遗韵,也正是其当时浸淫传统的用心之作。虽然这类书迹与其后来中、晚年风格成熟的典型“赵字”相比,尚未完全形成所谓自家面目,但却自然清新、生机时见,正如《画禅室随笔》卷一所收董其昌《跋赵子昂书过秦论》中指出的那样:“吴兴此书,学《黄庭内景经》,时年三十八岁,最为善者机也。成名以后,隤然自放,亦小有习气。于是赝书乱之,钝滞吴兴不少矣。”而据赵氏同时代的袁桷所记:“承旨公作小楷,着纸如飞,每谓欧、褚而下不足论”,则更可见赵氏的功力和自信,故当年鲜于枢就一言论定:“子昂篆、正、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
现存《鲜于府君墓志》原拓二本中,上图本曾为清代著名碑版收藏家陆恭松下清斋旧物,故陆氏婿潘世璜之子遵祁所录《须静斋云烟过眼录》中有记:“松雪《鲜于府君墓志》,小楷书石刻,后有王良常跋。”后归著名金石鉴藏大家沈韵初,传至其子筱韵(毓庆),又转入叶昌炽之手,叶氏《语石》中曰:“元石至精之品有两本:一为宋仲温《七姬权厝志》,一为赵承旨《鲜于府君志》,皆希世珍也……《鲜于志》旧为沈韵初孝廉所藏,其子筱韵来修士相见礼,以此为贽,遂归余五百经幢馆。”而具体时间,则叶氏《缘督庐日记》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影印手稿本)有记:丁酉(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十七日,观汉石经残字、旧拓砖塔铭、赵子昂鲜于伯机墓志,皆沈韵初旧藏,小韵携来,铭心绝品也”,“七月廿九日,沈肖韵来……愿列门墙,以鲜于伯机墓志为贽。”虽然叶氏《奇觚庼诗集》卷下《题沈筱韵遗像》一诗开篇,又谓:“沈生沈生昔吾友,燕市来游岁辛丑。登堂贻我青琅玕,金薤灵文世稀有(筱韵脩士相见礼,以赵承旨所书《鲜于府君铭》为贽,旧拓孤本也)”,但据该集此诗编年,这已是癸丑(1913)年间的忆旧之说,今检《缘督庐日记》,辛丑(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间,确有沈肖韵到京来访并多有过往诸记,然皆未及拜师贽见之事,则叶氏后来诗中所忆,恐不如其当年日记所载准确。
叶氏得此,至为宝爱,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其由京官出为甘肃学政,即随身携往。晚清书画收藏名家裴伯谦曾撰《河海昆仑录》四卷,系其于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三月二十七日至次年丙午(1906)四月八日,由广州遣戍新疆时一路所记,该书卷二乙巳十二月初七日记其道经甘肃,在叶氏任所获见《鲜于府君墓志》之情形颇详:
初七日,晴,较冷。甘肃学政叶君昌炽借《落水兰亭》,托君禹约余一晤,谈陇右金石。午后往。出示所得松雪书《鲜于府君碑》并敦煌千佛洞书经画像……元《鲜于府君墓志》,松雪五、六分小楷,略兼行意,《乐毅》十之六,《黄庭》十之四,与余藏《赵府君阡表》墨迹相同而字较大、行较疏,正力追钟、王时作,高于《闲邪公》数倍,明以来书家极称之。惜石亡,世不多见。提学出示一册,前有梁山舟楷书题签,山舟书墓志多用其意。后有王良常小楷一跋,称为松雪盛年经意之笔,并言松雪小楷《过秦论》三篇黄绢墨迹,为其友人张叔佩所藏,因欲寿母,求售于人。以为可惜,力阻云云。提学言此帖系沈韵初旧物,殁后其子出售,得之。生平收碑片数千种,惟此帖为箧中之冠。
而叶氏《缘督庐日记》该年中,亦可见相关之记:“十二月初二日,刘君瑜来,未见。从裴伯谦处索得赵子固《落水兰亭》真本……伯谦在岭南以四千金得之。许留案头,摩挲一日。”“十二月初七日,刘君瑜偕裴伯谦来,携示赵松雪十札墨迹。亦出《鲜于府君墓志》同赏,并以酒泉所得敦煌千佛洞唐写经卷子,请其鉴定。亟叹为真唐经生笔。惟佛像三帧,皆不许可。长谈至暮始别。”
叶氏之后,此本《鲜于府君墓志》如何最终入藏上海图书馆,目前似未见明确记载。上世纪五十年代古典文学出版社所刊潘景郑先生《著砚楼书跋》中,有其庚辰(1940年)六月八日所撰《五百经幢馆碑目稿本》一跋,文中述及:
右乡先辈叶鞠裳先生《五百经幢馆碑目稿》五册,分地系碑,都三千六百八十一种,而五百经幢不与焉……据先生日记,晚年以五百经幢归诸刘氏嘉业堂,而碑刻石墨,则以三千金归诸刘氏聚学轩。比孙君伯渊得刘氏石墨七千余通,叶藏亦在其中。因从伯渊假读其目,所藏石墨,以题名造像为夥,分地系目,凡八十余处。就余藏箧勘之,得其十之二三……内资州简州石刻十种,及江夏洪山寺建塔石刻十二种,犹是先文勤公旧物。今吾家旧藏,已如云烟,予殚心搜罗,二十年来,已逾万石之数;乃先生所藏,可补箧中未有者,又不下二千种。恨余绵薄,不能举而有之,展翫斯目,徒令人增望洋之感而已。
此跋之后,又有潘先生补记:“按叶氏藏箧,旋向伯渊购得,并聚学轩所藏,都万数千种,近已悉数捐诸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矣。”只是叶氏当年向刘氏聚学轩出让所藏碑拓时,不仅已将五百经幢分开另售,且类似《鲜于府君墓志》这样的精品,好像也不在其中,刊布于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所编《历史文献》第十九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的《缘督庐遗札(下)》 (夏颖整理)中,有叶氏当年将所售碑版装箱打包后托曹元忠转交刘氏一札,谓:“寒舍藏碑大小九笥,前日遣奴子归併,叠为四板箱、一皮箱,又一包大于牛腰,共六大件,特专车送呈。闻聚翁出游,俟其归时,敬祈转为检交。偏劳至极,心感无既。此累累者访求三十年之久……弟所以弃如敝屣者,其中苦衷当亦聚翁之所鉴及,无待弟之赘言。崦嵫已迫,心愿早了一日是一日,务祈鼎言转达,不胜感荷。”与《缘督庐日记》丙辰(1916年)六月十一日所记,基本一致。而札后附言,则为日记未及:“再,旧拓精本、剪裱有题跋之本,言明不在内,重分亦承聚翁慨允赐还,将来编目之时,尚须拜求分神代为留出。以陇石为多,有多至二十余分者。赵乾生藏石亦有三四分。先此奉告。”又今存上海图书馆并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叶鞠裳先生手写五百经幢馆碑目初稿》中,亦未见《鲜于府君墓志》。不过此“碑目初稿”虽有“潘景郑收藏印”朱文长方印及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馆藏诸记,但却多有与潘跋所述不相符者:首先只是未钉稿一叠,并未分装五册;其次是著录格式并非“分地系碑”,而是杂列碑刻名目,每条下各注其所在地名;再者目中不仅多录经幢,且碑刻、造像、墓志、画像、题名等均也有不少,应该不是潘先生所跋之本。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同时又著录另一种南京图书馆藏《五百经幢馆碑目》稿本,已影印收入2017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经检阅,其为方格写本,共分五册,分地系目,以造像题名居多,间附少数经幢等,但未见潘先生题跋及收藏印记,惟第一册前另有一纸,为统计“缪氏所无叶藏所有之数(查至唐末止)”,计由汉、晋直至隋、唐,“共一千一百十八种”。据《缘督庐日记》所记,叶氏当年出售碑拓,曾应买家要求编制目录,则此本亦可能即当时用以检核点交者。今通检全目,仍无《鲜于府君墓志》。
北大本虽自“适李择善铭曰”至“又命其友余”共六面约三百三十字不知何时缺失,由清代沈梧抄补,然因椎拓较早而文字泐损仍有少于上图本者,其中最重要的是:上图本第五开中“君讳光祖,字子初”之“祖”字已泐,而北大本(第八开)则完好;第八开中“拂衣而去”之“去”字剪失,“次淮安,卒于舟中”一句“淮”字和“于”字之间石花仅占一字之位,则“安”“卒”二字必失其一,而北大本(第十二开)“去”字未失,“安”“卒”二字全,且不损。此外,上图本第四开(北大本第五、第六开)中“高祖为始金初”之“为”字、“门人多第而己独不第”之“独”字,第六开(北大本第八开)中“尽刮去险纵之习”之“尽”字,以及第九开(北大本第十三开)中“与宋张忠定公”之“定”字等皆漫漶,而北大本均存。除此之外,北大本后又有沈琴斋、唐翰题、沈梧、刘铁云诸家题跋,多具研究价值。如抄补者沈梧题跋中,就拈出据该志后盛彪题记,可推知鲜于枢确切生年;又如由唐翰题三则题跋及所引相关文献中,知此志原石曾“在保定一士人家”,而唐氏于同治五年丙寅(1866)从沈琴斋处获此不全之拓后四年(庚午,1870),又“得见全文拓本于湖州钮君兰畹所”,“以索值过昂置之,后为川沙沈韵初中翰购去。每一展读,怆然久之”。再据唐跋记其所见全文拓本中“君讳光祖”之“祖”字已漫漶等特征,则应当即为今上海图书馆藏本。凡此种种,似皆可备一闻,且能证吴湖帆先生跋其自藏《金拓蜀先主庙碑足本》中所言:“唐鹪安与先外祖沈公韵初为金石至交,故咸、同间凡古碑旧拓,大江以南,不归沈氏,即入唐氏。余所收数十种中,两家曾经收贮者,殆过半矣。”

国图本《伊阙佛龛碑》沈志达题跋(局部)

北大本《鲜于府君墓志》沈琴斋题跋

张廷济跋沈志达旧藏《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张廷济跋沈志达旧藏《灵岩寺碑》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书后所附“图版说明”中“鲜于光祖墓志”条下,谓北大本曾经沈树镛(韵初)收藏,此不知何据;又谓该本后抄录周士甫题记并自跋之“琴斋”即沈树镛,则误。此“琴斋”即唐翰题跋语中所称“沈琴斋学博”者,当为道(光)、咸(丰)间江苏吴江人沈志达,国家图书馆藏何氏清森阁旧物唐褚遂良《伊阙佛龛碑》后,有其楷书长跋,署“咸丰五年七月初十日欧斋学人沈志达并书”,钤朱文“志达”“欧斋”、白文“沈氏图书”三印。比照北大本《鲜于府君墓志》后沈琴斋题跋,字迹相同,当出自一手。另友人仲威先生《善本碑帖过眼录》 (文物出版社2013年7月)中著录今在上海图书馆的顾文彬藏本《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后,亦有咸丰五年六月立秋日欧斋学人楷书题跋,并附原件图版,不仅字迹与国家图书馆藏《伊阙佛龛碑》及北大本《鲜于府君墓志》后沈氏所题一致,且其所钤朱文“欧斋”、白文“沈氏图书”二印,也与前述沈氏跋《伊阙佛龛碑》所用三印中的后二方,完全相同。而上图顾文彬旧藏《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后沈氏题跋首行右下的“琴斋审定”朱文方印,又正是北大本《鲜于府君墓志》后沈琴斋录周士甫题记下所钤之印。顾文彬藏本《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后,另有金石学名家张廷济为沈氏所题一跋,款曰:“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八月十三日,吴江芦墟沈兄琴斋先生属书,嘉兴竹田里七十八岁老者张廷济叔未甫。”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中所收《灵岩寺碑》后张廷济“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八月十三日为吴江芦墟琴斋沈兄先生书”之跋,竟又在同年同月同日,故二者格式、用纸也几乎一样,而张氏此二跋中署款后钤印,除“眉寿老人”一印前者用白文方印、后者为朱文长方印之外,另一“嘉兴张廷济叔未甫”白文方印,也完全相同。
北大本《鲜于府君墓志》后,又有晚清喜收金石碑拓的抱残守缺斋主人刘铁云(鹗)题跋二则,除评说其所见赵(孟頫)书墨迹、拓本之外,其中一则并记“光绪乙巳(1905)年二月初八日归抱残守缺斋,价三十五元”,与《抱残守缺斋日记》 (中西书局2018年6月影印手稿本)中“乙巳日记”二月初八日所记“周谨生送《鲜于子初墓志》来,合《杜顺和尚记》为五十元也”,正属一事。后刘氏被清廷遣戍新疆,宣统元年(1909)卒于戍所,藏品尽散,此本又为其友人、也是儿女亲家的罗振玉所得。作为近世收罗金石碑拓极富的研究者,罗氏曾列此《鲜于光祖墓志》于其《墓志征存目录》之中,以备访求。今由北大本内“上虞罗氏”“叔言集古”二印,知其最终亦得遂愿入手。